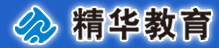如丧考妣:消逝的“手艺” 和假装的乡愁
三本书,盐野米松的《留住手艺》、赤木明登的《造物有灵且美》和祝小兔的《万物皆有欢喜处》。这三本书说的都是“手艺人”,虽然面临着“老手艺”的行将消逝,也引动了他们内心的惆怅,就像盐野米松写到的:“如今,童年记忆中的各条街道里匠工们作业时的工具所发出的声音没有了,他们的作坊没有了,隔窗观望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。那是因为这些职业已经不在我们身边,只一个世代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是怀着一颗憧憬和向往的心,观望过匠工做活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,也是为这些职业不复存在而深感遗憾的一代人的代表。”三本书都选择了诚实的“记录”,而不是廉价的抒情,悲情,甚至滥情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,既然“手艺”联系着是我们的日常生活,那么“手艺”的生与灭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,只是现代化以后,手艺从个别性死亡,变成毁灭性的灭绝。如果留心观察,现在给老“手艺”的消逝唱挽歌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生活在手艺人中间的青春前史。因此,当消逝的“手艺”成为我们时代的乡愁,那个痛点更多不在手艺人身上,而是舞文弄墨的文人自己身上,是生活在城市的文人们怀旧病发作了。当我们把怀乡病和现代性焦虑安放在“手艺”和“手艺人”中间,手艺的器物之美之温度之文化,放在今天的工业产品面前,引动的哀伤是很能自怨自艾。于是,消逝的手艺翻作成假装的乡愁,手艺人的故事也被偷换成自己的“致青春”。但真实的手艺人可能要简单得多,以我做例子,我的外公就是一个修伞磨剪刀的手艺人,我父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石匠,石匠在我们这一代唯一的工作就是把磨浅磨钝的磨盘凿深。在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故乡外出读书工作的时候,他们的手艺基本已经没有用武之地。在他们的手艺“无用”之前,消失得更早的应该是补锅焗碗之类的手艺。我承认是“现代”让他们失业,但我也看到其实这些手艺人也很淡然地接受了他们的手艺逐渐的“无用”。手艺无用后,这些乡村的手艺人大多安心地做了一个农人。本来乡村的手艺人,就是亦农亦手艺的。
就像宗白华指出的:“中国人对他的用具(石器铜器),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,以图生存,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,表达对自然的敬爱,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,秩序,它内部的音乐,诗,表显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。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。”我不否认,“手艺”因其是传统文明的寄居之所,是文化的,又是审美的,且和日常生活相关,其消逝所带来的怅惘和隐痛则更和我们的心灵痛痒相关。回到我们生活的当下,我也不否认,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恃强凌弱、消灭差别的时代。那些曾经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思想、景观、器物以及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,有的已经消逝,有的行将消逝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不同文化、不同艺术的冲突、交融以至生灭成为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件。但是,就像祝小兔的《万物皆有欢喜处》看到的,一些和我们新生活休戚相关的新手艺和新手艺人,在我们身边,在城市出现。所以,我认同盐野米松说的:“社会的变迁,势必要使一些东西消失,又使一些东西出现,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惯性,但是,作为我们,更应该保持的恰恰就是从前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珍重的那种待人的‘真诚’”;亦如赤木明登所言:“每一段故事诞生的地方,都有一种‘美’存在。”我不希望这种“真诚”和“美”被假装的“乡愁”污染和淹没。

- 上一条高三的第一次月考 该如何准备?2015-09-15
- 无下一条记录